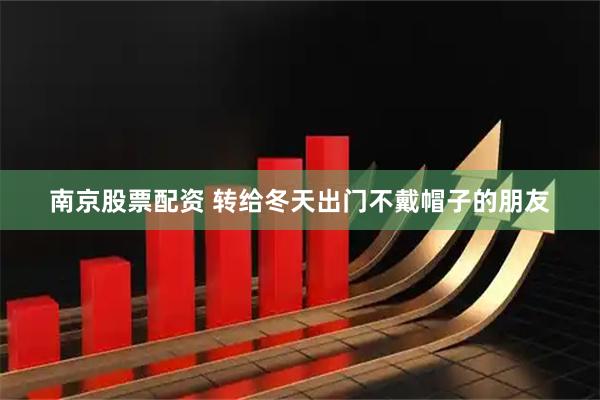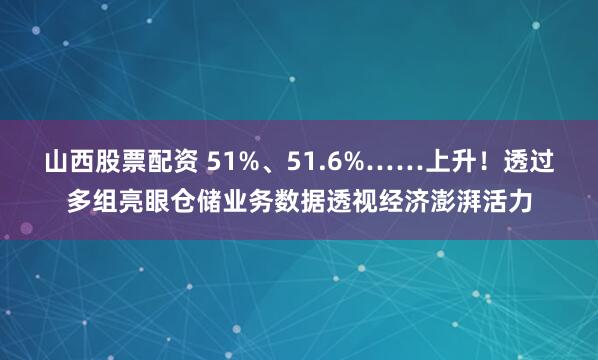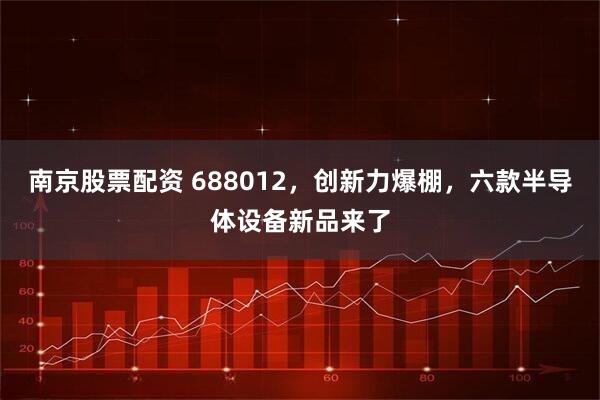“1978年8月,北京,京西宾馆——要是晋中那一仗慢半拍南京股票配资,咱们恐怕就得在太原城下流更多血。”王新亭把搪瓷杯放在桌上,手指轻敲杯沿,声音不大,却把茶室里几个老首长的思绪,一下子拉回到1948年的那个酷热六月。

彼时华北第一兵团刚刚结束临汾苦战,整编、补员、教练一项都没落下。阎锡山却自鸣得意,放话说共军“元气大伤”,根本无力再战。说实话,外界也有人信了他的判断。可徐向前没有。元帅收到毛主席电报后,只回了四个字——“原地打阎”。简短,却把晋中与太原的命运定了基调。六月十二日凌晨,部队北渡汾水,枪机上的油还没擦干。
阎锡山那边也忙得很。他把主力的五分之四拱到晋中,目的直白:抢粮、囤粮、稳住后勤,然后死守太原,等国际局势天翻地覆。要形容阎的算计,“熬到天下乱,再图复国”大概最贴切。为了这点算盘,他给赵承绶下令:“粮食先运,部队断后。”在军事史里,这句话后来成了反面教材。

再看华北第一兵团,兵员缺额依旧,装备也比阎军差一截,甚至还有不少临汾伤员缠着绷带上了路。中央给了一条“保险线”:先歼一两个师就行。参谋处有人松了口气。可徐向前只是抬头看了看地图,说:“不够。四到六个师,没这数不算完。”并补了一句:“出了问题我担。”屋里一下子静了,没人再反对。王新亭后来回忆,这一刻看见的是“铁板釘钉的劲头”。
决心高,部署必须跟上。徐向前先让主力在文水、交城一线做正面牵制,突然又把八纵、九纵拉成纵队,向北猛插。方向直指太原南郊,把阎军回城的路死死卡住——这是标准的“关门打狗”。阎锡山的大后方出乎意料地空荡。他手下参谋提醒:“共军意在截路。”阎却回:“新编之师,岂有此能?”事实很快打脸。

第一阶段,华一兵团硬碰阎军主力,顺手拔掉晋中外围要点,随后一个急转身,几乎是昼夜兼程地往北切。天气闷热,官兵平均一天进四十公里。有意思的是,很多老四方面军出身的指挥员说一句顺口溜:“汗珠子摔在地上一个响!”疲劳极限被一次次刷新。八纵先头团到达太古南侧,正面不足一个营,却硬是抢下制高点。赵承绶闻讯,急调部队北撤,想突围回太原。可道路早被切断,他只能在太古、徐沟、榆次之间来回撞围。徐向前抢到主动,他给部下定了三句口令——“咬住、靠近、贴皮。”距离越近,阎军炮火优势越难发挥。
那几天,徐向前本人高烧到39度,坐在担架上批文件。王新亭请示:“部队脱力,能否停两天?”回答干脆利落:“不行,爬也要过去。”电话挂断,他又对身边警卫说:“三十二小时,这是底线。”没人敢耽误,就这么扛着。
六月二十四日夜,太岳部队赶到董村,直接堵在敌纵队前头。敌军猛冲,火光映红麦田。太岳41团阵地被打出缺口,连长裴诚带剩下的九个人顶住。第二天早晨阵地仍在,团参谋长看了看,哑着嗓子说:“稳如泰山。”这个称号后来写进战史。

包围圈形成后,问题却来了:兵力不够,防线有缝。徐向前索性把战法改成“分片围点”,谁守到谁算——典型的弹性封闭。敌人抓空子往北冲,一支就撞在八纵的卡脖子阵地上。王新亭实在撑不住,再次打电话申请撤下休整。徐帅拄拐赶到前沿,他没多话,只说一句:“再挺五分钟。”岗楼里的无线电把这句话反复播,像钉子一样定住士气。五分钟过后,第二梯队赶到。几条溃口被堵严。赵承绶见突围无望,六月三十日晚率部投降,全线崩溃。
战果相当惊人:一个月时间,歼敌正规军七万余,杂牌三万余,俘获将官十六名,缴枪、炮、骡马压得公路满满当当。阎锡山的“粮仓”和“机动部队”一夜之间没了影,只得闷在太原城里。毛主席电报用了“极大”二字褒奖。毛主席原稿写“很大”,后来亲手改成“极”。细节不多,却足见分量。

顺带一提,这仗结束后,华北一兵团的称号被定了下来:徐向前任司令,周士第任政委。晋中一役也被许多军史学者视作徐帅的“封神之战”。原因不只是战术灵活,更关键在于那份“不达目标决不罢手”的狠劲。王新亭说:“徐司令平日话不多,看着和气,可真打起来根本不松手。你要是退,他一句话就把你拉回来;你要是上,他敢把后手全压给你撑腰。”老将一句调侃:“不服不行。”
有人问我,这场战役的最大启示是什么?我的看法或许直接:第一枪想得再好,不如最后五分钟咬得更紧。徐帅挂在嘴边的那句“熬过去”不是口号,而是作战原则。任何强敌,只要被拖进崩溃边缘,坚持者就成了胜者。

晋中啃下来了,太原再硬,也只剩时间问题。事实也如此。四个月后,太原解放,阎锡山灰溜溜飞到台湾。回头算账,他丢掉的不仅是粮仓,更是整个战略时机。王新亭说:“徐司令这一狠,是救了山西,也是救了我们自己。”这话我信。山河易改,硬骨头难得。徐向前把“硬”演绎到极致,所以老兵们才会几十年后还边喝茶边念叨——“徐帅沉默寡言,打起仗来真狠啊!”
君鼎证券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